美丽的表象——解读耶利内克的小说《情人》

耶利内克像
耶利内克也许不是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但毫无疑问是最具争议的一位。指责她、漠视她的与支持她、赞美她的人几乎一样多。[1] 有评家说“她制造混乱,挑起矛盾。冷酷、仇恨和恶意嘲讽就是她的本色。……文学批评接近她的方式只有小心翼翼和犹豫不前。只是在提及她的语言天赋时,批评界才会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有时也会是赞赏。”[2] 耶利内克在1975年发表小说《情人》(Die Liebhaberinnen)的时候,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很好的戏仿反讽之作”[3],是“耶利内克关于妇女解放的寓言”[4],是“关于爱之恨的社会客观报告”。[5] 另一方面,也有评论家认为作品“令人恶心”[6],有“社会窥阴癖”的倾向[7],并且“对作品人物缺乏关爱”[8],甚至还有人将一大堆贬义词抛给这部作品:“不够人道,不够女人,刻薄,恶毒,冷酷,灭绝人性。”[9]
从上面的评论不难看出,部分评论家的愤怒似乎是由于女作家独特的写作方式与他们对于一个女作家该如何写作的预期大相径庭而引起的。他们评价作品的标准似乎也来自于伦理和道德领域,而不是审美范畴。很明显,耶利内克的写作方式让他们很不习惯。耶利内克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承认:“促使我写作的力量,也就是促使我写作的利比多,完全是基于个人经验[10]而产生的感情……我的确是怀着极大的仇恨在写作”。以仇恨为写作动力和视角的作品不免让人觉得尖刻、恶毒,这也正是耶利内克最受批评界诟病的地方。但是,耶利内克的这种“仇恨写作”绝不是个人私愤的发泄,她并不认为这种“个人经验”纯属偶然,她一直在思索背后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她实际上是布莱希特的同道,她希望读者能够通过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某些矛盾和弊端有所认识。或者按照她自己的话说,“我还要一再地考虑,如何将这一感情(仇恨)加以抽象。于是我就把它带到普遍的社会层面上来,以便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而她处理作品素材的方法就是“讽刺”。她说:“我一直都在利用讽刺进行写作,即对现实进行扭曲和变形……我所追求的并不是去客观描写现实,因为根据布莱希特的看法,这样做的人实际上得到的也永远只是一张肤浅的现实的转印画而已;我追求的是一种被夸大的、被扭曲变形的现实,以便能够更为透彻地探讨现实,从而将现实变得更加现实。”不难看出,耶利内克所奉行的“现实主义”不是自然主义的、完全忠于生活的写作方式,而是故意对素材和主题进行夸张和典型化处理,以达到更好的讽刺效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会宣称,《情人》是她“第一部直接以现实为主题的长篇小说”。[11]

小说《情人》首版封面
女人的命运:乡村与城市
在一次访谈当中,耶利内克曾把《情人》称为一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的小说”。[12] 虽然作家的用词暴露出她在确定小说主题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游移不定,但不可否认,这部小说以其对父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强烈的批判意识,而毫无疑问地具有了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
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年轻的女性,布里吉特(Brigitte)和葆拉(Paula)。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处理这两个人物的时候,特意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两个主人公被处理成两种对立的妇女类型:“理智型”的布里吉特[13]更为现实,更为冷静,能够为自己的目标做出牺牲;“感情型”的葆拉则是个容易脱离实际、耽于幻想的女人,憧憬着浪漫的爱情。对于生活的不同设想让她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布里吉特希望通过与电气技术员海因茨(Heinz)的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葆拉则想通过学一门手艺来改变生活,直到她爱上了伐木工埃里希(Erich)。最后布里吉特当上了“幸福”的家庭主妇;而与丈夫离婚的葆拉,最后不得不在内衣厂里干起布里吉特曾经干过的事情,当上了缝纫女工。从表面上看,叙述者故意用“好的榜样”和“坏的典型”[14]这样的用词来说明,布里吉特是生活的成功者,而葆拉则是失败的。但是,在这看似对立的两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的却是更为紧密的“内在联系”。
首先,两人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妇女。葆拉的父亲是收入低微的伐木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她本人则是缝纫学徒。而来自单亲家庭的布里吉特和母亲一样都是内衣厂的缝纫女工。
其次,两个人都不满于生活的现状,都对生活抱有更好的期待和憧憬。葆拉不想重复母亲和姐姐一样的命运,她希望通过学习裁剪手艺来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于布里吉特来说,她的工作干脆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而她想要的却是“真正的生活”。
再次,试图改变生活的美好愿望遭遇的却是不利于女人发展的社会现实,即父权制度的存在。葆拉所在的村庄坐落在象征着封闭与保守的山谷里面。需要指出的是,葆拉所在的村子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处在“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下,从社会意识来说,属于“传统父权社会”(或称“家庭经济时期的父权社会”)。因为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只受到来自父亲的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压迫和剥削。在那里,妇女只能接受十分有限的教育(最多初中程度),也没有真正的职业。女人,无论未婚还是已婚,除了未婚前可以有一段时间做消费品商店店员外(做店员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认识某个男人”),她们都只能扮演家庭经济时代妇女能够扮演的惟一角色:家庭妇女。妇女被剥夺了发展自己的机会,无论婚前还是婚后,等待她们的只能是被“父亲”奴役的命运。这一点在葆拉和埃里希的母亲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两个女人一辈子都在拼命地干活,最开始是伺候各自的父亲,婚后是伺候丈夫和孩子。而她们得到的回报却只有饱受摧残。而对于父亲来说,老婆和孩子还是供他发泄的渠道,是用来“殴打和辱骂的生物”。因此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很容易变成一个暴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埃里希的继父:“他对一切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就像是一个噩梦,漂浮在一切的上面,身体里面发出丑陋的嘶嘶声”。(第92页)

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情人》剧照
与葆拉的山村相比,城市里面“父亲”的角色似乎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体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工厂。在布里吉特的内衣厂里,女性所能从事的只能是缝纫工人和秘书,工厂的领导层则统统都是男性。这一工厂实际上象征着城市里面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剥削依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增加了新的方式而已。而这些方式我们可以总称为“资本主义父权制度”。[15] 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女性在生活与职业上受到丈夫和老板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例如对于婚后的布里吉特来说,海因茨既是丈夫也是老板,她不仅是他的“管家”、“清洁工”、“厨娘”和“带孩子的保姆”,同时还是他商店里的“人力资本”。同山村一样,城市里的女性依然没有获得真正发展自己的机会。虽然表面上看,妇女拥有了自己的职业,似乎拥有了独立的地位。但是这一美丽的假象实际上是用工作权利上的平等掩盖了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大部分女性,尤其是下层妇女,她们所从事的职业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收入较低的劳动;而那些相对收入较高的工作乃至重要的职位却都由男性把持着。
因此,被剥夺了发展机会、在经济上无法真正独立的下层妇女最终只能通过婚姻来获得安全感并确保自己的生活。父权制度的存在使得男女之间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女人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与奴仆,必须依赖于男人生活。对于女人而言,幸福只能通过婚姻来实现,更好的生活就意味着要“把握住一个有着更好未来的男人”。布里吉特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才会不择手段地一定要嫁给海因茨。而深受大众传媒影响的葆拉则幻想着通过学习裁剪手艺来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她能够坚持下去,也许可以得到个人幸福。但是大众传媒在她脑子里还形成了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裁剪不能让女人幸福,只有男人能让女人幸福”,这使她最终放弃了学习,转而追求起杂志上所渲染的“爱情”。
但是,父权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男人掌握主动权,女人必须使出全身解数来获得男人的欢心。由于两个主人公都不名一文,所以她们惟一能够争取男人的手段就是她们的身体:一方面她们将身体作为劳动力,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来赢得男人及其家人的好感;另一方面,她们直接用身体来迎合男人的生理需要。对于主人公来说,“爱情”没有甜蜜的感觉,它“只能算是一种工作”,是一个为了争取男人而饱受屈辱和折磨的过程。她们必须一再地掩饰自己的感情,而去迎合男人及其家人对自己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蹂躏。
于是,妇女在父权制度下最终只能走进这样一个悖论:婚姻是她们获得个人幸福的惟一途径,但是她们经过不懈努力争取到的婚姻却根本无法带来幸福。对男人的依赖性决定了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幸福,而完全取决于所嫁的男人。叙述者用“偶然”这个词来解释两个主人公命运存在差异的原因,而这不过是主人公无力反抗现实、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代名词而已。
综上所述,生活在迥异的环境中的两个不同类型的女人,她们的生活道路看似相反,实际上却都通向同一个被践踏、被蹂躏的悲惨结局。因为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还处于父权制度的统治下,那么女人的命运就只有一种,即被剥夺发展自我机会、只能通过婚姻来确保安全感与物质生活、最终只能充当家庭妇女、总是被男性压迫和剥削、最终被现实彻底毁掉的命运。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尽管男人也可以是可怜的猪猡和各自境遇的牺牲品,……但是他总能找到另一个比他更可怜的人,那个人就是他老婆。”[16]

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情人》剧照
所有人的失败:爱情和亲情
耶利内克创作《情人》的目的也是为了向当时女性文学的一些倾向作出回应。她认为,“当前女性文学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一味地抱怨和诉苦,同时痛骂男人。她们应该在美学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手段,并且向前更进一步。”[17] 耶利内克这里所说的“更进一步”就是要求作家不能停留于表面,而应该通过作品去揭示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制度上的原因。对于制度问题的关注也正是女作家创作的一个基本理念。而在探讨造成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原因时,她还在父权制度之外,找到了另外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即资本主义制度。[18] 在服膺马克思主义[19]的耶利内克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中,它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统统“物化”,并将其异化为赤裸裸的利己打算。为了突出这一问题,作家特意将小说中的人物都设定为社会下层,因为生存问题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一种经济行为,生存斗争和效益最大化成了每个人生活的基调。为了凸显人际关系的这种异化,作家又特别选择人类理应最无私的两种情感——爱情和亲情——作为突破口,用强烈的反差来制造反讽效果。
在处理人物的爱情问题上,耶利内克是一个绝对的“唯物主义者”。她曾经承认,“爱情的经济决定性是我小说一个最重要的视角”。[20] 在小说里,男女间的“爱情”就是一种经济关系,完全依照市场规律在运作。由于父权制度的存在造成的男女立场的不同,这一经济关系又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从男性的角度看,女人是商品,男人是买家。为了体现女人成为商品这一现实,叙述者还特地使用了诸如“质量”、“消费”、“质量等级”“市场价值”等一系列的经济术语来形容女性的地位。而从女性的角度看,女人是投资方,男人则是投资对象。投资方投资所期待的回报就是获得安全感和确保物质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人物,无论男女,实际上都是带有一定“市场价值”的客体。而最能体现客体“市场价值”的因素就是金钱与财富。所以对于埃里希和海因茨来说,“一个有钱的女人”才是他们希望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对于女人而言,她们的“真命天子的情况应该要么与自己相同,要么比自己稍好一点,最好是好很多”(第61页)。从上面不难看出,男女在选择“商品”或“投资对象”时都遵循同一条经济原则,即效益最大化。
与爱情类似,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也同样被表现为一种功利行为:很多父母生小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到了老年不至于孤单”。而长大之后的孩子则是父母手中具有经济功用的活工具:在家是廉价的劳动力,出去工作则可以为家里赚钱。葆拉的母亲希望女儿能够待在家里“帮她一起干活”。而埃里希则是家里人的“能够进行生产的财产”,他的主要功能就是干家里的粗活,同时还要做伐木工人为家里赚钱。埃里希的母亲还要求儿子如果有了钱,一定不能忘了他们。后来埃里希的父母之所以反对他和葆拉的婚事也是因为她无法给这个家带来好处。而这也正是海因茨的父母不喜欢布里吉特的理由。他们培养海因茨的目的是希望他为他们建一个独户住宅来安度晚年。但是他们这样教育孩子的最终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孩子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也变得功利起来:布里吉特从来不在母亲那里帮忙,因为“那就意味着把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亏损的小公司里。毫无出路,毫无希望”(第15页)。而海因茨则利用机会把老迈的父母打发进了养老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并且变成了一种负担。

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情人》剧照
事实上,无论葆拉所在的村庄,还是布里吉特周围的圈子,人与人之间只有一种情感是真实的,那就是“仇恨”。而这种相互仇恨的现实又在父权制度下被进一步激化。如前所述,作为制度的受益者,男人对于比他低的等级(女人和孩子)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在对待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等问题上变得简单粗暴,变成奴役和虐待家人的暴君,变成完全不顾别人感受的自私鬼。在耶利内克笔下,家庭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战场。资本主义—父权制度的存在使得下层民众无论男女都在工作和生活中饱受压迫和剥削,对生活产生了很强的挫败感,而发泄这一挫败感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家庭暴力。而家庭的权力分配则决定了实施暴力的模式:作为家长的“父亲”在老婆身上发泄不满,夫妻双方又同时折磨处于最低等级的孩子,而无处发泄的孩子“就会把折磨小猫、小狗和小孩当作替代品”。家庭暴力在酒精的刺激下愈演愈烈,家庭的亲情也在暴力中一点一点泯灭。
在金钱与拳头教育下长大的年轻人,有的会对爱情和婚姻有着特别的渴望。“在耶利内克的小说里面,爱情这一概念表现出人物对于温情与和谐的实际需要。这一点在主人公葆拉的设想里体现的最为明显。”[21] 正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缺乏温情与和谐,葆拉才会寄希望于自己的爱情。但是未婚先孕的她等来的却是父母的毒打、男友家长的反对、村人的羞辱和男友的扬长而去,这一连串的打击彻底毁掉了她的精神世界:“葆拉的心里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爱的痕迹。如果葆拉的心里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恨,越来越大的仇恨。”(第128页)
另外一些人则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埃里希从小就不断遭到母亲、外婆、继父和一起伐木的同事的暴力虐待,他的内心已经被“仇恨”填满:“埃里希很想打死他的爸爸妈妈”,而他爱的能力早就被暴力泯灭,“埃里希根本就没有爱可以分给别人”。他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倒是和葆拉的婚姻改变了他的地位,成为了一家之长。这也让他找到了“小猫小狗”之外更好的发泄途径。成家之后的他“终于获得了统治一个人的权力……这是一种他要尽情享受的全新感觉,有时候他还会发出一些毫无道理的指令”(第177页)。就这样,他们的家庭也开始重蹈父母那一辈的覆辙,变成了战场。
来自单亲家庭的布里吉特对待爱情的态度则比较复杂:一方面,她需要通过婚姻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她的爱情观有很强的功利性;另一方面,她也希望能够在“爱情”那里获得平时得不到的温情与和谐。所以在她看来,她所能够取得的“最佳值”就是找到一个既爱她又有出息的人。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布里吉特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为了一定的目标做出牺牲。所以当海因茨及他的家人一再地粗暴对待她,并且打破了她所试图建立的平衡时,她必然放弃“爱情”而选择“生活”:“她的牙齿因为仇恨而格格作响。在这么多的仇恨面前,就算是最持久的爱情也要沉默。这时候海因茨已经由爱情变成了最严肃的义务,从娱乐变成了工作。”(第43页)虽然海因茨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让布里吉特“恨”他,但是她还是不择手段地要他娶她。而在婚后,布里吉特所能享受的只是物质占有带来的“快感”,而“仇恨已经彻底吞噬了她的内心”。
海因茨市侩的父母一直不断地告诫他,要他把眼睛“盯在真实的东西上面”,也就是财富和地位。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方式最终使得“海因茨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本源”,变成了一个绝对自私的人。和埃里希一样,他也没有去爱别人的能力。不同的是,埃里希不是没有爱可以给别人,而是根本无法爱上别人,因为他惟一爱的人就是他自己。对他而言,别人都是他踩着用来往上爬的阶梯。一旦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所以他在得到了父母的全部积蓄之后,就立即把他们扫地出门。对于女人,海因茨首先想到的也是用途。他最希望找到一个“有钱的女人”,这样他就可以“很快自立,并且拥有自己的商店”。他对布里吉特根本就没有爱情可言,有的只是性欲。因为布里吉特不是“有钱的女人”,他根本就没有动过娶她的念头。所以当他认识了家境良好的苏茜(Susi)之后,就转而追求苏茜。但就是在此期间,他依然将布里吉特当作发泄性欲的对象。
小说的四个主人公分别代表了在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下长大的四种年轻人类型。他们注定要成为感情上的失败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被资本主义-父权制度全面侵蚀的社会环境,那样的社会里最终发展出来的只能是冷酷的人际关系,而正是冷酷的人际关系彻底扭曲了他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并且毁掉了他们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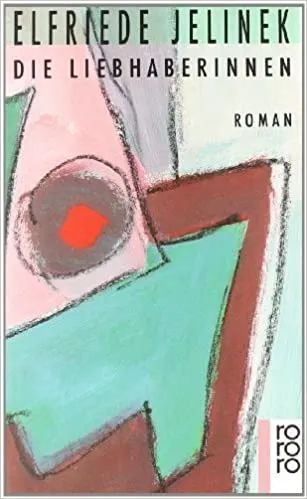
《情人》封面
通俗小说的批判:神话与自然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耶利内克在构建这部小说的时候故意采用了通俗小说的写作风格和模式。在题目上,“情人”这个名词很容易让人对这部小说抱有通俗的阅读期待。在写作模式上,女作家采用了通俗小说惯用的套路,尤其是爱情小说和乡土小说。在写作主题上,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通俗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爱情[22],而这也是《情人》的主题。在写作风格上,通俗小说一般会使用较小、较具体的词汇,简单的句子结构,有很强的口语化倾向,经常使用成语和惯用法[23],而这些特点《情人》也都具备。尽管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是耶利内克决不是在进行通俗小说创作,相反,她是在对通俗小说进行反讽性戏仿,这主要就表现在她对小说写作模式和主题的处理上。
妇女题材的通俗小说通常把女人区分为好坏两种类型。好女人都拥有浪漫的爱情,最后走向幸福的婚姻。而坏女人则会试图利用“性”去控制男人,最后等待她的只有不幸。很多这样的小说都会重复“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让贫穷但纯洁的女孩最终赢得爱情和幸福。耶利内克在小说一开始也把两个主人公分成了“好的榜样”布里吉特和“坏的典型”葆拉,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这样的“二分法”仅仅是形式上的,实质上两个主人公都是父权制度的牺牲品,都是感情上的失败者,她们只学会了仇恨。
在一般的爱情小说里,人物经常会由爱生恨,爱恨不分。在耶利内克的小说里,爱与恨也同样紧密不分,只不过表现为另外一种关系:

布里吉特从来不敢说自己饿了或渴了。等到后来海因茨饿了的时候,布里吉特也饿了。海因茨和布里吉特共有一个身体,永远保持同步。两个人连成一体。
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情况。
布里吉特恨海因茨恨得要命。

在这里,耶利内克故意套用基督教关于男女之情的最高设想,即夫妇“两人一体”(《旧约·创世纪》第2章第24节)的说法。实际上,引文的第一部分就体现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女人一直在强迫自己适应男人的愿望和要求。而“仇恨”才是女人自发和主动的情感。引文的第一部分和最后一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作者故意在两个部分之间加入一句“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情况”作为连接语。这样一个褒义的句子连接的却是两个消极的内容:屈从和仇恨。通过这样的处理,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不管事物的表象看起来多么和谐、统一,它们实际上却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在这里,爱与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只有“恨”才是人物真正的感情,而“爱”不过是女人向男人表示臣服的权力游戏而已。
性欲是爱情的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通俗文学通常会把两者描写成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和谐关系。而在耶利内克那里,爱情和性欲从一开始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埃里希和海因茨都没有爱情,只有性欲;而葆拉和布里吉特则只渴望爱情,不懂性欲。如前所述,无论是葆拉,还是布里吉特,她们都希望能够在“爱情”那里获得平时得不到的温情与和谐,吸引她们的仅仅是“爱情”本身。虽然性爱与爱情无关,而且给她们带来的也仅仅是“难受”和“疼痛”,但是由于她们不名一文,在爱情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她们只能利用自己的身体来取悦男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性”也是女人向男人表示臣服的另一种权力游戏。
耶利内克最具讽刺意蕴的写法出现在她对“白马王子”的颠覆上。两个女主人公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她们从困顿的生活中拯救出去,从而开始“真正的生活”。但是她们盼来的“白马王子”却是海因茨和埃里希这样两个情感上的“残废”:一个只爱他自己,一个根本不会爱。女主人公只能徒劳地在这样两个男人身上费尽心思,根本无法得到想要的“幸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耶利内克之所以选择通俗小说作为反讽对象,是因为通俗小说把爱情、性爱、幸福等一系列日常生活的概念神话化了。所谓“神话”[24],按照罗兰·巴特的定义就是“去政治化的话语”。话语中蕴含的“神话概念”,例如爱情,它在语言学层面上拥有的“意义”并非是“现实”的,而只是“有关现实的一种知识”。在神话学层面上,“神话概念”将它语言学上的意义“变形”,使其失去其历史特征,这也就是所谓的“神话化”。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解,“神话化”就是“将历史转变为自然”,或者按照耶利内克自己的说法:“用自然代替历史”,即脱离社会的、现实的框架,把历史的、人为的、可变的、偶然的东西当作是永恒的、自然的、固定的、必然的东西。“在人类交际的所有层面上,神话所起的作用都是将‘非自然’转化为‘伪自然’。”[25] 作为深受罗兰·巴特影响的作家,耶利内克一直致力于揭开这些神话美丽的外表,向读者展现它们所掩盖的父权压迫与经济决定的真实,从而对通俗小说所散布的爱情和幸福神话进行无情的嘲讽与解构。

罗兰·巴特像
耶利内克对通俗小说的批判同时还在于她也沿用通俗小说的方法,并使用“自然力”或“命运”这样的字眼来解释人物的发展。例如葆拉把所遭受的一切都看作是“自然的力量”:“葆拉清楚,自然的力量要比人的力量强大。就像人无法与自然抗争一样,人也无法与这一自然的某一法则抗争……葆拉注意到,在自然法则面前,她是多么的渺小。她经常会说,人在原始的自然力面前能做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做不了。昨天电视里的一部教育片就是这样说的。”(第138页)在这里,人为的社会因素被当作是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这种“神话化”的想法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屏蔽掉了变革社会现实的可能性。这正是“神话”的意图所在,即把世界变成“一成不变”的世界,将人们“禁锢”在特定的思维领域内。[26] 而这也正是耶利内克的作品力图去消解的东西,因为葆拉的悲剧绝对不是命运的捉弄或是自然的安排,而是制度造成的恶果。虽然葆拉也曾经试图去摆脱村子里“自然循环”的束缚,但是正是关于爱情和自然的“神话”观念麻痹了她,让她失去了斗争的力量,让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最后只能屈从于社会的压迫。
不难看出,耶利内克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批判,一种针对西方社会体系的文化批判。她批判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两点,即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和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是这两种体制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时她还试图利用对通俗小说的反讽性戏仿和批判来让读者对小说保持批判性距离,从而获得启蒙的效果。正是由于内容上的深刻与反讽艺术的娴熟运用,所以才有人将这部小说称为“耶利内克早期创作的最高峰”。[27]
[1]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间,耶利内克作品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她已经被视为当代德语文学最出色的一位女作家。有研究者认为,她的作品完全可以与另外两位奥地利著名作家彼得·汉特克(Peter Handke)和托马斯·伯恩哈特(Thomas Bernhard)等量齐观。参见Matthias Konzett,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Dissentin Thomas Bernhard,Peter Handke, and Elfriede Jelinek,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0, p. 95。尽管如此,对她的作品不屑一顾的人也还是大有人在。作家马丁·莫泽巴赫(Martin Mosebach)就对女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感到“莫名惊诧”,认为她是“西半球最愚蠢的一个人”。在他看来,耶利内克之所以能够得奖可能是由于她政治上“反法西斯”的立场。瑞士巴塞尔剧院经理米夏埃尔·申德赫尔姆(Michael Schindhelm)则认为耶利内克的作品“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那是一种在政治上鼓吹和鼓动的文学,和全球化的精神是相悖的。耶利内克是一个过时的艺术家。”参见 Berthold Seewald,Gemischte Reaktionen,in Die Welt,08.10. 2004。
[2] Annette Doll, Mythos, Natur und Geschichte bei Elfriede Jelinek:eine Untersuchung ihrer literarischen Intentionen, Stuttgart: M und P Verlag,1994,S. 9.
[3] Tobe Joyce Levin, gesprächsthema: die liebhaberinnen von Elfriede Jelinek, in mamas pfirsiche-frauen und literatur, Mǜnchen, 1977, H. 8,S. 61.
[4] Ria Theens, Im Stakkato-Rhythmus der Akkordarbeit .Elfriede Jelineks Emanzipations-Parabel, in Rheinische Post, Dǜsseldorf,30. 08. 1975.
[5] Hedwig Rohde, Sozialreport vom Liebeshass, in Der Tagesspiegel,Berlin, 11. 01. 1976.
[6] Heinz Beckmann,Der Gegenstand Paula,in Rheinischer Merkur,19.09.1975.
[7] Hans-Jǜrgen Richter, Emanzipiertes als Voyeure, in das da, 11. 11. 1975.
[8] Elke Kummer, Du,unglǜckliches Österreich, heirate, in Die Zeit,14.11.1975.
[9] Sigrid Löffler, Jedes Werk von ihr ist eine Provokation. Interview mit Elfriede Jelinek, in Bǜcher. Brigitte Sonderheft, 1983, S.27.
[10] 耶利内克父母的关系比较紧张,她的父亲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就患了很严重的脑病,最后精神错乱而死。而很有野心的母亲则对女儿的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耶利内克很早就有心理问题,不得不定期接受心理检查。尽管如此,心理上的问题并没有影响她智力上的发展,她一直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有关女作家的生平参见Elisabeth Spanlang,Elfriede Jelinek:Studien zum Frǜhwerk,Wien: VWGÖ, 1992, S. 16-33.
[11] [12] [16] [17] Mǜnchner literaturarbeitskre is,gespräch mit Elfriede Jelinek, in mamas pfirsiche-frauen und literatur, Mǜnchen, 1978, H. 9/10,S. 173,S. 174,S. 174,S. 174.
[13] 布里吉特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与之同名的德国最大的一份妇女时尚杂志,杂志所代表的是一种时髦、中庸的妇女形象,这似乎也与人物的性格特征相吻合。
[14] Elfriede Jelinek, Die Liebhaberinnen, Berlin: Verlag Volk und Welt,1978,S. 30. 以下小说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加注,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15] “父权制度”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是指父亲的统治权力。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男性统治并不仅限于此,它同时还包括丈夫、男上司,社会机构以及政治经济生活中男性领导者对于女性的统治。之所以选择这个名词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表现出男性对于女性压迫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参见Maria Mies, Patriar-chat und Kapital. Frauen i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eilung, aus dem Englischen ǜbersetzt von Stefan Schmidlin,Zǜrich: rotpunktverlag, 1988, S. 55.
[18] 需要指出的是,葆拉所在的山村和城市一样都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山村的封闭与保守造成了它的某些社会意识,例如妇女问题,还停留在传统父权社会阶段。
[19] 耶利内克曾于1974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后由于对党内政策的不同意见以及党内对她作品的抨击,她在1991年退党。参见Elisabeth Spanlang,Elfriede Jelinek:Studien zum Frǜhwerk,Wien: VWGÖ,1992,S. 212。
[20] Josef-Hermann Sauter, Interviews mit Barbara Frischmuth, Elfriede Jelinek und Michael Scharang, in Weimarer Beiträge 27,H. 6, 1981,S. 113.
[21] Margret Brǜgmann, Schonungsloses Mitleid,Elfriede Jelinek:Die Liebhaberinnen, in: Margret Brǜgmann, Amazonen der Literatur, Studien zur deutschsprachigen Frauen literatur der 70er Jahre, Amsterdam: Rodopi Verlag,1986,S. 146-172,hierS. 151.
[22] [23] Peter Nusser, Romane fǜr die Unterschicht, Groschenhefte und ihre Leser, Stuttgart: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73,S. 37, S. 25f.
[24] 在罗兰·巴特看来,“神话”是一个双重符号系统,即语言学和神话学双重意义上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本身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终端,也是神话学意义上的发端。在语言学意义上,它是一个完整的符号,有自己的能指和所指;但是这一语言符号又变成了“神话”的能指,它与“神话”的所指一起构成了“神话”。在神话的层面上,这一语言符号又被称为“神话概念”。参见Roland Barthes, Mythen des Alltags, ǜbersetzt von Helmut Scheff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4, S. 92-94.
[25] [26] Roland Barthes, Mythen des Alltags, ǜbersetzt von Helmut Scheff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4, S. 130,S. 147.
[27] Elisabeth Spanlang, Elfriede Jelinek: Studien zum Frǜhwerk, Wien: VWGÖ, 1992, S. 296.